我的QQ號,是二零零九年在廣東省珠海市斗門鎮(zhèn)落下的。像一枚生銹的圖釘,按進(jìn)了那段年月里,后來就再?zèng)]拔出來過。 零九年,聽著就往下墜。不是后來那些一幾年,輕飄飄的。零九,零字有個(gè)拖長的尾巴,九字又沉甸甸地收住,合起來,像車間墻角那桶用廢了的黃油,黑膩膩的,凝固在那兒,時(shí)間久了,就和水泥地長在了一起。 那時(shí)我在斗門鎮(zhèn)東頭的偉創(chuàng)力電子廠。日子是流水線上流過來的。傳送帶是條銀灰色的河,我們站在岸邊,伸手,從流動(dòng)的塑料盤里撈起一塊綠色的板子,再伸手,從身旁的料盒里,用指尖拈起一顆米粒大的東西。那小東西有兩條細(xì)腿,閃著金屬的冷光。你得看準(zhǔn)板上那些更小的孔,對準(zhǔn),輕輕一按。咔噠,一聲極輕微的響,幾乎被機(jī)器的轟鳴吃掉。它便站住了,焊在了那密密麻麻的金色線路之間,成了那片沉默疆域里一個(gè)永久的居民。一天要按幾千次。起初手指尖是疼,后來是木,最后就沒了知覺,只看見它們還在動(dòng),起,落,起,落,像斷了線的木偶手,被風(fēng)吹著。 田伏明睡我上鋪。武漢人,生得白凈,尤其一雙眼,眼皮薄,眼珠子是清亮的褐色,看人時(shí)涼絲絲的。但他不能提老家,一提,那眼里的涼就化了,底下有熱乎氣涌上來。他說山里雨后松樹下的蘑菇,胖墩墩的,頂著油亮的褐色小傘。他說溪澗里的石頭,夏天踩上去也冰腳脖子。他說這些時(shí),我們正咽著廠里的飯。飯硬,菜是水煮的,漂著幾星油花。 是他拉我去網(wǎng)吧的。忘了是哪天晚上,宿舍里電視開著,吵得很,卻不知道在吵什么。他探下頭,頭發(fā)亂蓬蓬的,說,走,給你弄個(gè)QQ。 網(wǎng)吧名字真忘了。大概叫星空或者極速這類,透著股廉價(jià)的幻想。在廠子后面,隔一條總也干不了的馬路。推開那扇貼著褪色游戲海報(bào)的玻璃門,氣味是一下子撲上來的。先是冷氣,粗糙的,帶著灰塵味的涼。但這涼很快就被更厚實(shí)的東西吞掉了。那是上百臺(tái)機(jī)器和身體一起發(fā)熱,烘烤著塑料、海綿、橡膠墊、還有地上潑灑的不知什么液體,混合出來的,一種溫吞吞的悶味。里面攪著煙味,不是好煙的香,是廉價(jià)煙絲燒不盡的嗆;汗味,年輕男人被流水線榨過一遍后,從工裝深處透出的微餿;還有角落泡面桶里隔夜湯汁隱隱的酸。你得愣一下,讓鼻子適應(yīng),才能在這混沌里找到自己的呼吸。 田伏明熟門熟路,在靠窗地方給我找了個(gè)機(jī)子。窗外是街,對面小店霓虹缺了筆畫,一閃一閃,像個(gè)喘不過氣的病人。一個(gè)婦人坐在三輪車邊削菠蘿,黃色的皮螺旋著垂下來,在路燈下軟塌塌的。 里面暗,光來自屏幕。一塊塊幽藍(lán)的方塊,浮在黑暗里,映著一張張年輕的臉。那些臉朝著同一個(gè)方向,被藍(lán)光從下往上照,下巴尖,眼窩深,瞳孔里只有兩個(gè)小小的、跳動(dòng)的亮方塊。他們很安靜,只有手指敲鍵盤,噼里啪啦,噼里啪啦,聲音密得像夏天最急的雨打在鐵皮屋頂上,沒有間斷,只是響,反倒襯出更大的靜。我剛下白班,骨頭里還留著傳送帶那種均勻的震顫,坐進(jìn)那張人造革開裂、露出黃海綿的椅子時(shí),能感到上一任主人留下的體溫,溫乎乎的,貼著我的腿。那感覺有點(diǎn)怪,像是坐進(jìn)了別人剛離開的生活里。 田伏明已經(jīng)點(diǎn)開了那只小企鵝。屏幕光在他臉上滑動(dòng)。想個(gè)名兒,他盯著閃爍的光標(biāo)說。 我怔住了。名兒?在車間,我是拉線三組第七工位。在宿舍,我是下鋪。在工資條上,是一串?dāng)?shù)字。我叫什么?窗外是異鄉(xiāng)黏糊糊的夜,口袋里是幾張新鈔。未來?未來像遠(yuǎn)處海上的霧,看得見,摸不著。胸膛里堵著東西,硬硬的,卻又空得慌。 不知怎么,嘴里就冒出四個(gè)字。 君臨天下。我說。 聲音輕,自己聽著都虛,像呵出去的一口氣。 田伏明手指停了停。他側(cè)過臉看我,那對清亮的眼睛定了兩秒。然后笑了,有點(diǎn)意外,有點(diǎn)明白。行啊,他說,手指又敲起來,夠威風(fēng)。 君,臨,天,下。四個(gè)方頭方腦的字跳進(jìn)框里。它們躺在花哨的網(wǎng)頁上,忽然有了種陌生的鋒利。我的臉騰地?zé)崃恕:孟裥牡鬃詈~、最不敢見光的那點(diǎn)東西,自己爬了出來,晾在了這渾濁的燈光下。頭像是他幫我挑的,找了半天,選中一個(gè)戴皇冠的獅子側(cè)影,鬃毛像火一樣炸開,眼神睥睨著,背景是燃燒的城堡。就它了,配你的名兒。密碼,他讓我用生日加老家電話區(qū)號,這樣丟不了。 就這樣,在斗門鎮(zhèn)一個(gè)彌漫著泡面味和汗酸氣的網(wǎng)吧里,在別人余溫未散的破椅子上,我成了君臨天下。 我的王國,起初是荒的。好友列表里,孤零零站著幾個(gè)名字,都是從廠里這片海浮上來的島嶼。阿強(qiáng)叫斷弦的吉他。其實(shí)他連吉他有幾根弦都不知道,手指粗短,適合握扳手。他只是喜歡斷弦這兩個(gè)字,說聽著就有心事。湖南仔李偉,叫孤獨(dú)的狼??伤f話細(xì)聲細(xì)氣,皮膚白,笑起來會(huì)臉紅。他總在半夜的群里念叨,家里寄來的辣醬快吃完了,那辣醬裝在大玻璃瓶里,上面浮著厚厚的紅油。還有個(gè)廣西姑娘,我沒見過,在包裝車間,叫折翼天使。她的頭像是流淚的天使,翅膀斷了一邊。她不怎么說話,偶爾說一句,句尾總帶個(gè)啦字,輕輕的,軟軟的。 我們在這片新地方,開始說話。話都帶著車間的氣味。是松香燒熔的甜腥,是機(jī)油蹭在袖口的滑膩,是食堂大鍋菜里永遠(yuǎn)煮不爛的菜梗子味,是站了八小時(shí)后,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,深深的倦。 最常說的,是一句最簡單的問話。 在嗎? 就這兩個(gè)字。打出來,發(fā)送。心就提起來了。眼睛盯住屏幕右下角那個(gè)灰色的小喇叭。耳朵在網(wǎng)吧嘈雜的背景音里,努力分辨那一聲獨(dú)特的嘀嘀。 那咳嗽聲,有時(shí)來得快。有時(shí)要等很久。等的時(shí)候,你會(huì)看見屏幕保護(hù)跳出來,深藍(lán)色的海底,幾條顏色俗艷的魚,張著圓嘴,傻傻地游,永遠(yuǎn)游不出去。你會(huì)聽見旁邊的人猛地拍鍵盤,罵一句臟話,踢開椅子走了。心就跟著那腳步聲,一點(diǎn)點(diǎn)沉下去。冷氣好像更重了。 有時(shí)候,在你幾乎要關(guān)掉對話框時(shí),嘀嘀聲卻突然響了。清脆,帶著電流的毛刺感,像夜里一塊冰裂開。那灰色的頭像,瞬間被點(diǎn)亮。于是,兩個(gè)被流水線隔開、被異鄉(xiāng)夜晚泡著的人,就在這虛擬的亮光里,用拼音,用不熟的手指,開始結(jié)結(jié)巴巴地對話。話都很實(shí)在,實(shí)在得帶著毛邊。今天線上機(jī)器又壞了,罰站半小時(shí)。食堂的肉薄得透明。明天發(fā)工資,去不去吃頓好的。 QQ空間,是我花心思布置的地方。我用了好幾個(gè)晚上,研究怎么換皮膚,怎么加?xùn)|西,怎么讓音樂自己響起來。最后選了一個(gè)底色,是近乎黑的深紫,上面撒著銀色的光點(diǎn),像冬天夜里凍人的星空。背景音樂,我選了貝多芬的命運(yùn)。必須是開頭那幾聲,當(dāng)當(dāng)當(dāng)當(dāng)。音量調(diào)到最大,在網(wǎng)吧油膩的耳機(jī)里炸開。好像只有這樣,才能壓住周遭現(xiàn)實(shí)的一切,才能讓我覺得,自己摸著了一點(diǎn)兒莊重的東西。 我在空間的日志里寫字。不敢叫文章,叫胡話。寫流水線是時(shí)間的模具,把我們澆鑄成一樣的形狀。寫螺絲釘?shù)泥l(xiāng)愁是旋轉(zhuǎn)的,一圈一圈,擰緊自己,也擰死遠(yuǎn)方。現(xiàn)在看,酸,酸得倒牙??赡菚r(shí)不覺得。那時(shí)寫得虔誠,手指在鍵盤上敲得生疼,好像每個(gè)字都能變成一塊磚,讓我在這虛無的地方,壘起一點(diǎn)什么。 紫藤花就是那時(shí)出現(xiàn)的。她來我的空間,在我每篇胡話下面,留下淺淺的腳印。話不多,淡淡的??茨銓懧萁z釘,我對著屏幕笑了。我在質(zhì)檢位,每天用放大鏡看焊點(diǎn),看得久了,覺得每個(gè)焊點(diǎn)都像一只孤獨(dú)的眼睛。你的星空皮膚,讓我想起老家夏夜的打谷場,累了一天躺下,睜眼就是那樣的天,星星低得要掉下來砸臉上。不過我們不看星星,我們只看明天天氣好不好,要不要搶收稻子。 我們沒見過。沒視頻,沒電話,也沒在食堂里找過對方。但我們知道,在這片龐大的、轟鳴的工廠森林里,還有另一雙眼睛,在相似的疲憊之后,望著同一片虛擬的星空。這知道,讓壓著的夜,似乎松了一點(diǎn)點(diǎn)。 零九年的冬天,嶺南的冬天是濕冷,往骨頭里鉆??删W(wǎng)吧里的人,卻多了起來。煙霧更濃,咳嗽聲也多了,干干的,帶著胸腔的回音。好像屏幕里那點(diǎn)光,真能取暖;好像那虛擬的連接,真能擋點(diǎn)風(fēng)。 那年春節(jié),好多人沒回去。車票難買,也有人不想回?;厝プ鍪裁茨兀坑靡荒甑睦?,換親人小心翼翼的打量?年三十晚上,網(wǎng)吧擠滿了人??諝鉁啙岬孟裰?,但每張年輕的臉上,都有一種奇異的、發(fā)紅的光。 我的QQ群里,熱鬧極了。我們這些沒地方去的人,在數(shù)字世界里團(tuán)聚。發(fā)著網(wǎng)上找來的、閃爍的電子煙花圖片,用最大的字刷新年快樂。用夸張的表情包互相拜年,說著恭喜發(fā)財(cái)這樣吉祥而空洞的話。窗外的斗門鎮(zhèn),靜悄悄的,遠(yuǎn)處偶爾炸響一兩個(gè)鞭炮,像試探,馬上被更大的靜吞沒。窗內(nèi),這片由機(jī)器低鳴和屏幕藍(lán)光構(gòu)成的地方,卻在上演一場滾燙的、孤獨(dú)的盛宴。 那一刻,君臨天下這個(gè)名字,像個(gè)冰冷的笑話,懸在我頭頂。我統(tǒng)治什么?統(tǒng)治一群漂泊的軀殼,統(tǒng)治一片隨時(shí)會(huì)斷電的沙堡。我的權(quán)杖是鼠標(biāo),我的皇冠是耳機(jī),我的疆域是這間充滿腳臭的地下室?;恼Q,又心酸。 可它又那么真。像寒夜里,幾個(gè)人擠在一起呵出的白氣。雖然弱,雖然一下就散,但那一刻的暖,是真的。我們用這些從現(xiàn)實(shí)縫隙里抽出的絲,把自己和外面那個(gè)刮著冷風(fēng)的世界,暫且隔開。哪怕只隔一層透明的繭,也能喘口氣。 說實(shí)話,我的QQ號,從來沒被盜過。它像一只最忠心的老狗,守著那點(diǎn)微弱的數(shù)字家門。但它以一種更慢的方式,在失去。先是風(fēng)中蒲公英李姐的頭像,再也不亮了。聽說她兒子要上學(xué),她辭了工,回湖南老家陪讀去了。接著,中原一點(diǎn)紅,那個(gè)總愛在深夜談金庸的河南小伙,在群里說,蘇州有個(gè)新廠,工資高幾百,他買了張站票,走了。最后,連田伏明也走了。他們那條線整個(gè)裁掉。他接到家里電話,說有急事,匆匆收拾了那個(gè)小牛仔包,連頓像樣的送行飯都沒吃,就在某個(gè)我上白班的早上,不見了。像一滴水,蒸發(fā)了。 潮水,就這樣靜悄悄地退去。不是轟隆一聲,是慢慢地,一寸一寸矮下去。智能手機(jī)來了,微信那個(gè)綠色的圖標(biāo),簡單,干凈,沒有QQ那么重的裝飾,那么多心事。它像個(gè)合手的工具,出現(xiàn)在一個(gè)大家都累了、不想再復(fù)雜的時(shí)候。 紫藤花的頭像,是從哪天開始灰的?記不清了。沒有告別,沒有留言,就像她來的時(shí)候一樣靜。某次點(diǎn)開列表,才發(fā)現(xiàn)那朵小小的紫花,暗了許久。像夏夜里一顆熟悉的、不太亮的星星,你習(xí)慣了它的位置,某天抬頭,卻發(fā)現(xiàn)那片天空了一塊。你甚至不能確定,它是否真的存在過。 群里的消息,從一天上百條,變成幾天一條,最后徹底靜了。像一顆心跳,漸漸緩了,慢了,停了。最后一條信息,停在很久以前,是個(gè)過時(shí)的笑話,沒人回,孤零零掛著,像秋后野地里最后一棵草稈,在風(fēng)里抖。 我的QQ空間,也徹底荒了。深紫色的星空皮膚,早失效了,變回一片死灰,像廢棄廠房的水泥地。那曾經(jīng)讓我血熱的命運(yùn)交響曲,鏈接早斷了。偶然點(diǎn)開,播放器只是一片沉默的空白,進(jìn)度條無聲走完。 最后一次登錄,是很多年后了。在一個(gè)沒事的周日下午,陽光很好,我坐在舒服的椅子上,用著薄薄的電腦。處理完事情,手指無意識(shí)地動(dòng)。忽然,那串?dāng)?shù)字——那串我以為早忘了的、長長的數(shù)字——清晰地浮現(xiàn)在腦子里。 手指自己動(dòng)了,在瀏覽器里,一個(gè)鍵一個(gè)鍵,敲出了那個(gè)幾乎陌生的網(wǎng)址。 登錄。 界面很陌生,花哨,擠滿了看不懂的東西和閃動(dòng)的廣告,像個(gè)穿著時(shí)髦、表情冷淡的陌生人。我手忙腳亂關(guān)掉彈窗,憑著一點(diǎn)模糊的記憶,找到那個(gè)被擠到角落的入口。點(diǎn)了進(jìn)去。然后,遲疑地,點(diǎn)開那年今日。 一條沉在時(shí)間河底的記錄,被撈了起來。 是我自己寫的。忘了是哪年。配著一張模糊的照片,大概是舊手機(jī)拍的,一片晃動(dòng)的、金屬的冷光。 記錄下面,我這樣寫: 我盯著手里這塊板子,看了整整一個(gè)下午。那些金色的線,一條一條,交叉,平行,又交叉,在燈下亮得刺眼。它們畫得那么精細(xì),那么復(fù)雜,像一張地圖,一張畫滿了路和城的地圖。我看了又看,眼睛都看花了??墒菦]有一條路,是標(biāo)著出口的。一條都沒有。 那句話,像一顆埋了太久的啞彈。一直躺在那里,被歲月的泥沙蓋著。在這個(gè)平靜的、和過去毫無關(guān)聯(lián)的下午,它里面的引信,卻忽然燒到了頭。 沒有聲音,但有什么東西在腦子里轟了一下。 窗明幾凈,暖氣很足,窗外是北方疏朗的冬天。可我的指尖,猛地傳來一陣清晰的、冰涼的觸感——是電路板光滑堅(jiān)硬的表面。鼻腔里,瞬間充滿了松香和焊錫熔化的甜腥氣。耳朵里,嗡嗡地響起了流水線永不停歇的低鳴。 那個(gè)取名君臨天下、在油膩鍵盤上敲下絕望的年輕人,他的惶恐,他的憋悶,他那點(diǎn)用像素皇冠和燃燒城堡撐起來的、可憐的驕傲,隔著厚厚的時(shí)光,突然赤裸裸地、手足無措地站到了我面前。我們隔著這么多年對望。我看著他一無所有卻挺著的倔強(qiáng),他看著我擁有許多卻時(shí)常感到的空。彼此都覺得對方陌生,卻又在眼底最深處,看到同一種悲涼的底色。 我退出登錄。關(guān)掉網(wǎng)頁。 那串?dāng)?shù)字,連同它身后那個(gè)早已倒塌風(fēng)化、被時(shí)代沖得面目全非的王國,重新沉入無邊無際的數(shù)字黑暗里。屏幕暗下去,黑得像深潭,映出我如今這張有了皺紋、卻還留著舊日影子的臉。 它不再是一個(gè)社交軟件工具了。它成了一個(gè)遺址。是我個(gè)人歷史里的一座龐貝城,被一場叫時(shí)代的火山灰瞬間埋住,所以留下了那一刻最鮮活也最疼的樣子:那里的空氣怎么振,光線怎么流,指尖下的油膩怎么粘,希望怎么像蝸牛觸角一樣伸出又縮回。那里有機(jī)油和紅燒牛肉面混在一起的復(fù)雜氣味,有深夜里眼眶的干痛,有肌肉記憶的酸麻,更有那種在龐大、堅(jiān)硬、漠然的現(xiàn)實(shí)面前,試圖用幾個(gè)字、一個(gè)虛名、一片自己騙自己的地方,為自己撐起一點(diǎn)尊嚴(yán)的,渺小、笨拙、又那么悲壯的勁兒。 可它還在那兒。不是讓我用來懷念青春那種輕飄飄的詞。是為了作證。 真的有過那么一群人,在被機(jī)器節(jié)奏切碎的生命縫里,在螺絲和焊點(diǎn)的微小空隙中,用這樣一串隨手可得、毫無個(gè)性的數(shù)字,這么笨拙又這么認(rèn)真地,給自己悄悄加冕,和別人短暫結(jié)盟,朝虛無的時(shí)空,發(fā)出過微弱卻清楚的信號:我在。我在這里。我這樣活過。 那個(gè)想君臨天下的少年,終究低了頭,學(xué)會(huì)了在生活的溝里走路,算著得失,磨平棱角。那些曾在我這片虛擬星空下亮過一下的斷弦吉他、風(fēng)中蒲公英、紫藤花,也早就被各自的命運(yùn)河水沖得不知去向。加冕的禮堂塌了,結(jié)盟的旗子爛了,信號消失在宇宙巨大的靜默里,連一點(diǎn)回聲都沒有。 但,那試圖加冕時(shí)指尖冰涼的抖,那結(jié)盟時(shí)隔著屏幕感到的一點(diǎn)暖,那信號發(fā)出時(shí)胸膛里幾乎要炸開的擂鼓聲——沒有全散。它們被這串冰冷的數(shù)字刻了下來,成了我身體里一塊消化不掉、也排不出的結(jié)石,沉在心底最暗的河床底。每次生活的暗流涌過,每次時(shí)代的潮聲隱約傳來,它就在那看不見的地方,被水帶動(dòng),輕輕滾一下,硌著我,用它早已磨圓、卻還是堅(jiān)硬的邊角,提醒我:你曾是,而且永遠(yuǎn)是,那座孤城廢墟上,最后一個(gè)沒脫下盔甲的、沉默的守城人。 現(xiàn)在,我的世界里有更多更方便、更光滑的地方。手指一劃,信息像瀑布瀉下來;指尖一點(diǎn),聲音和臉立刻出現(xiàn)。一切都太快,太有效率,像一條更高級的、無菌的、安靜的流水線,準(zhǔn)確輸送一切,也沖淡一切??稍僖矝]有哪個(gè)地方,像那個(gè)簡陋的、彌漫著鐵皮味和汗酸氣、響著鍵盤聲和命運(yùn)叩門聲的王國那樣,讓我覺得,自己曾那么真實(shí)、那么具體地用全部的感官——用眼睛的澀,用指尖的油,用鼻子的濁,用胸口的悶,用那顆年輕心臟笨拙卻劇烈的跳——掙扎過,喘息過,實(shí)實(shí)在在地活過一場。 那個(gè)叫君臨天下的年輕人,他從沒君臨過什么。他最后被生活的泥沙裹著走了,學(xué)會(huì)沉默,學(xué)會(huì)承受,流進(jìn)更寬也更模糊的人海,成了里面一張平靜的、不容易被認(rèn)出的成年人的臉。 但他真的,在某個(gè)快要被流水線吞掉、被異鄉(xiāng)夜淹沒的時(shí)刻,在滿是泡面味和煙味、混著希望和絕望的溫?zé)釢釟饫?,給自己,踉踉蹌蹌地,舉行過一場沒觀眾的加冕。那頂像素格的皇冠,早化沒了。但加冕那一刻,心臟撞碎肋骨似的捶打,指尖冰涼固執(zhí)的顫抖,喉嚨里哽住的、滾燙的氣,卻通過這串沒有生命的數(shù)字,微弱而固執(zhí)地,傳了下來。直到今天,在這個(gè)一切都好像定了型的下午,還能讓我捧著熱茶杯的、已經(jīng)沉穩(wěn)的手,不由自主地,輕輕一顫。 這大概,就是這串?dāng)?shù)字,對我全部的意義了。 它不是通向任何人的橋。它是一座小小的碑,立在我來路的荒草里,碑上只有數(shù)字,沒有名字,風(fēng)吹雨打,字快磨平了。它也是一塊胎記,長在記憶的皮上,顏色暗,形狀怪,平時(shí)被衣服遮著,看不見。但你自己知道,它就在那兒。在某些完全沒防備的時(shí)候,比如聽到一段帶著舊時(shí)電流雜音的老歌調(diào)子,聞到某種像當(dāng)年網(wǎng)吧門口老榕樹氣味的、潮濕的土腥氣,或者,僅僅是手指無意識(shí)地、像當(dāng)年敲鍵盤找路那樣,空懸著,輕輕敲著光亮的桌面時(shí)—— 它會(huì)忽然醒過來。 帶著那個(gè)遙遠(yuǎn)年代的、全部的、粗礪的體溫和實(shí)實(shí)在在的氣味,輕輕地,沉沉地,硌你一下。
?著作權(quán)歸作者所有,轉(zhuǎn)載或內(nèi)容合作請聯(lián)系作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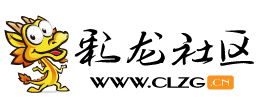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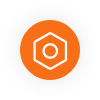
暫無評論,快來評論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