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體發(fā)膚,受之父母,不敢毀傷,孝之始也。
——《孝經(jīng)?開宗明義》
臉上開始長(zhǎng)青春痘,下巴上長(zhǎng)胡子,心里面藏了個(gè)漂亮電影明星胡思亂想的那年,我去了滇東北一個(gè)銅礦工作。
這個(gè)銅礦藏在金沙江半山腰一條狹窄的山溝里,壁陡的高山夾著一股溪流,冬春山坡荒蕪滴水成冰,風(fēng)吹石頭滿地跑,夏秋煙雨蒙蒙濕氣陰涼,要隨時(shí)提防泥石流和大滑坡。礦山天地雖小,卻也是一個(gè)活色生香的世界,在這個(gè)大山大川大石頭主宰的銅礦世界里,剃頭不叫“剃頭”了,改叫“理發(fā)”,去剃個(gè)頭變成了去理個(gè)發(fā)。在我看來,從農(nóng)村到礦山,從剃頭到理發(fā),跨越了不止一步。
選礦廠“公辦”的理發(fā)室很小,小到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個(gè)三十出頭四十不到的女理發(fā)師。聽墻根烤太陽(yáng)的人議論,女理發(fā)師原來在碎礦工段看皮帶運(yùn)輸機(jī),因?yàn)E情,被單位作了冷處理,從主要生產(chǎn)線下調(diào)到后勤輔助崗。時(shí)間久遠(yuǎn),記不得女理發(fā)師的名字了,只記得人們都習(xí)慣叫她“黑婆娘”,但她應(yīng)該不姓黑,叫的是她的皮膚黑吧。黑婆娘個(gè)子不高但苗條,五官也算清秀端正,眼睛水水的,燙了一頭港臺(tái)流行的波浪式發(fā)型,是選礦廠八十年代最新潮的女人之一。又據(jù)說,黑婆娘風(fēng)騷,換了崗位也改不掉“偷冷飯”的老毛病,理發(fā)時(shí)候除了說些讓人臉紅的話,還會(huì)不動(dòng)聲色地搞小動(dòng)作,比如彎腰用胸脯子摩擦帥哥的肩膀,或者不小心把梳子掉到帥哥腿根上,“啊呀”一聲伸手去抓。
我個(gè)子小,也不帥,頭發(fā)也長(zhǎng)得慢,差不多兩個(gè)月才理發(fā)一次,沒聽到黑婆娘傳說中的那些撩騷話,以及暗送款曲的小動(dòng)作。我反而覺得黑婆娘挺好挺親,笑瞇瞇地迎接每個(gè)進(jìn)理發(fā)室理發(fā)的人,她的笑臉純真、耐看,親切、大方,舉手投足像鄰家的姐姐。
三年后,我因?yàn)闃I(yè)余時(shí)間學(xué)寫了幾篇豆腐塊文章調(diào)礦機(jī)關(guān)部門寫更大塊的豆腐塊,理發(fā)的地點(diǎn)隨著變成了礦機(jī)關(guān)的“美容廳”。
礦機(jī)關(guān)理發(fā)室雖然名頭升級(jí),由“室”變“廳”,由理發(fā)變美容,面積也比選礦廠理發(fā)室大了好些,但基本布局和所承載的基本功能依然沒脫離剃頭和理發(fā)的范疇,所謂的“美容廳”也就是個(gè)洗頭剃頭的作坊而已。不同的是,理發(fā)的人變成了穿“中山裝”的機(jī)關(guān)干部和胸口插著鋼筆的知識(shí)分子,美容廳門楣上多了一副隸書體的對(duì)聯(lián),上聯(lián)寫著“進(jìn)門里蓬頭垢面”,下聯(lián)寫著“出門外白面書生”,沒有橫批。初讀時(shí)感覺怪怪的,礦山人好像和白面書生挨不上邊啊。
機(jī)關(guān)美容廳有一大一小兩個(gè)女理發(fā)師。年紀(jì)大的女理發(fā)師,來理發(fā)的男女老少都統(tǒng)一尊稱老嬢。老嬢背脊上拖著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辮子,工作中戴口罩,穿白大褂,理發(fā)的技藝高超,手上的協(xié)調(diào)性好,理發(fā)的人像木偶似被她“調(diào)度”的服服帖帖,七八分鐘就能搞定一顆人頭。理發(fā)的人對(duì)著鏡子看看,真還像對(duì)聯(lián)里說的“進(jìn)門里蓬頭垢面,出門外白面書生”。老嬢唯一不好的是理發(fā)時(shí)經(jīng)常和找上門的自家男人吵架,一個(gè)吧嗒著嘴吵,“你瓜妹子小氣得撒尿都用竹漏過濾,天天讓老子吃浠湯湯?!币粋€(gè)翻著眼皮罵,“你狗日的在外胡吃海喝營(yíng)養(yǎng)過剩,撬老娘的肚皮就像撬你家的祖墳。”兩口子的斗嘴話說得難聽,也不分場(chǎng)合,聽得我們一干子年輕小伙子面紅耳赤,心跳加快,恨不得拿坨棉花築起耳朵。
后來,就盡量找小女理發(fā)師理發(fā)。
小女理發(fā)師是個(gè)二十多歲的姑娘,名叫玉存,礦山技校烹調(diào)專業(yè)畢業(yè),因?yàn)椴说妒沟渺`活,一畢業(yè)就分到了礦機(jī)關(guān)理發(fā)室。玉存身材窈窕,但略微單薄,皮膚白白凈凈,披著一頭有些發(fā)黃的長(zhǎng)發(fā),說不上漂亮,但耐看,越看越好看的那種,看著看著就喜歡上了的那種。到了理發(fā)室,要先在門口探頭探腦查看一番,看見老嬢手里有活,而玉存剛好有空,這才趕緊進(jìn)去坐到玉存的理發(fā)臺(tái)子上。
我喜歡被玉存理發(fā),也怕被玉存理發(fā),每一次都會(huì)呼吸急促地等著玉存穿上白大褂,香噴噴地走過來,麻利地蓋上罩衣,再把手輕輕搭在頭上。比起老嬢,專業(yè)拿菜刀揮炒勺的玉存理發(fā)技藝稍微遜色,速度也不及老嬢快捷,但推剪出來的發(fā)型不差,自然而然,理了發(fā),就像沒理似的。這讓我常常暗自歡喜,仿佛玉存知道我喜歡留長(zhǎng)發(fā)似的,每一次都手下留情,只剪掉覺得多余的部分,還細(xì)心地加以解釋說,你的頭型不合適剪太短的發(fā)型,這樣子就剛剛好。
玉存的男朋友在十多公里外另外一個(gè)礦山工作,十天半月從山上下來看望她一次。小伙子濃眉大眼,長(zhǎng)相老實(shí),一笑一笑的,也不多言,規(guī)規(guī)矩矩坐在一邊等玉存下班。盡管我們幾個(gè)礦機(jī)關(guān)的小伙子都暗暗喜歡玉存,玉存也心知肚明,但她沒有給我們機(jī)會(huì)。遇到我們故意在她面前搞怪做樣子、裝情種,甚至跟她打情罵俏,也大大方方笑著搪塞過去,不給難堪,也不輕看。
兩年后,玉存調(diào)到男朋友所在的礦山工作了,以后再也沒有見她回來,但我們都記得玉存的善良和美好,記得玉存身上香噴噴的味道。那是一種很獨(dú)特、很樸實(shí)的味道,很好聞,很想聞。
許多年后,我才知道,那是一種叫“百雀羚”的味道,經(jīng)濟(jì)、實(shí)惠,礦山男人都普遍喜歡的味道。
作者簡(jiǎn)介
楊躍祥,筆名遙翔,白族,大理州祥云縣禾甸鎮(zhèn)人,中國(guó)作家協(xié)會(huì)會(huì)員。出版有散文集《黑哥哥黑姐姐》《父親的墓碑》和長(zhǎng)篇小說《銅草花開》《蒿子花開》《洋芋花開》?!躲~草花開》獲東川首屆“銅都文學(xué)獎(jiǎng)”金獎(jiǎng),《蒿子花開》入列中國(guó)作家協(xié)會(huì)少數(shù)民族文學(xué)重點(diǎn)作品扶持項(xiàng)目。
?著作權(quán)歸作者所有,轉(zhuǎn)載或內(nèi)容合作請(qǐng)聯(lián)系作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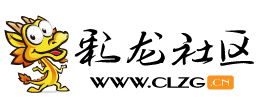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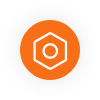
暫無評(píng)論,快來評(píng)論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