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親在我七歲那年的麥天去世,留下我們孤兒寡母相依為命。老屋的墻是土坯壘的,被煤油燈熏出大片大片的黑,我總疑心那些斑駁的紋路像地圖,有時是山脊線,有時是河流的支岔。當(dāng)夜晚來臨,煤油燈的燈芯爆出燈花時,母親會拿剪刀去剪,影子便順著墻皮簌簌地往下掉,掉進(jìn)我膝蓋上攤開的母親陪嫁時的《紅樓夢》里。 古人云:“書中自有千鐘粟,書中自有黃金屋,書中自有顏如玉?!笨梢?,古人對讀書的情有獨(dú)鐘。讀書最大的好處在于,它讓求知的人從中獲知,讓無知的人變得有知。讀書多了,心中所思所想,欲望需要釋放,世上便有了寫作這門手藝。 閱讀與寫作是我最喜歡做的事。 我的幼年其實非常不幸,對媽媽來說,整個世界就像一條沒縫好的棉被,棉絮總會露出來。而她的擔(dān)心就像針一樣,要把那些可怕的裂縫一一縫起來。這樣的一個不幸的童年,可能讓別的作家去寫,就會寫成一部苦難史、一部不堪去回想的家鄉(xiāng)史。但是當(dāng)我通過寫作重返自己童年的時候,我把我自己的家庭苦難全都擱下,或者忘記了,我已經(jīng)人到中年了,我可以理解生活的不幸,可以把自己家庭或者自己的苦難放在內(nèi)心中消化掉,而微笑地去面對自己的過往了。 那年我十三歲,在鄉(xiāng)里的中學(xué)念初一。母親趕集帶回來的舊書《水滸傳》,那本書是用半袋玉米換的,封皮上還沾著醬油漬。她搓著皴裂的手說:“總比看驢嚼草強(qiáng)?!斌H在院角嚼草的聲音的確單調(diào),但書里的馬蹄聲更響,豹子頭林沖雪夜上梁山的那章,我聽見瓦檐上的冰溜子都在叮咚作響。 煤油燈把母親的影子投在土墻上,像一座會走動的小山,她補(bǔ)著弟弟的褲子,針尖在發(fā)間劃過的弧度,和書里魯智深揮舞禪杖的軌跡莫名重合。我忽然發(fā)現(xiàn),墻上的黑影不僅能藏住衣服上的補(bǔ)丁,還能藏下北宋八十萬禁軍總教頭的悲愴。母親突然說:“燈油快熬干了?!蔽一琶Π褧摵仙?,卻見扉頁里的梁山好漢們正踩著墻縫的裂痕,逶迤消失在房梁的深處。 母親常在雨夜給我講父親年輕時候當(dāng)兵的故事。天上的雨水順著茅草屋頂滲了進(jìn)來,在搪瓷盆里敲出《西游記》里流沙河的水聲。母親說我的父親在戈壁灘上站崗時,月光會把整片沙丘澆鑄成閃亮的白銀盔甲。我摸著土墻上凸起的泥粒,恍惚看見唐僧的白龍馬正從墻根走過,駝鈴聲震落梁上的積灰。 故鄉(xiāng)的油茶林在谷雨時節(jié)最是黏人,絨毛似的白花沾在粗布衣襟上,總也撣不干凈。我蹲在供銷社改成的老書店門檻,膝蓋抵著開裂的朱漆木門,看斜陽把《林海雪原》的封面染成蜂蜜色。柜臺后的老楊頭在打瞌睡,竹煙筒磕在玻璃板上,驚落他藏青布衫前襟的煙灰。 這是三十年前的風(fēng)景。那時的舊書店像只塞滿過期果脯的陶罐,霉味里裹著油墨香。我常踩著三輪車轍印來,褲腳沾著麥田的泥星子。老楊頭總說:“孩子,你不要把書頁捏出鹽漬”,卻在我賒賬時,用指甲在賬本上劃出淺淺的月牙痕。那些月牙攢到中秋,就變成他塞給我的麻餅,油紙里還夾著半本《千家詩》。 記得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缺了封底,保爾在暴風(fēng)雪中推鐵軌的那章,正卡在供銷社老吊扇轉(zhuǎn)動的陰影里,鐵質(zhì)的風(fēng)扇葉切割著光斑,像把往事剁成碎片。那年母親在采石場傷了腰,我攥著書本走過碎石遍地的河灘,忽然覺得保爾推的不是鐵軌,而是生活碾過來的鐵轱轆。 鎮(zhèn)上人管書店的老楊頭叫“書蠹蟲”,他確實像蛀進(jìn)書堆的灰蛾子。有回暴雨沖塌了后墻,他抱著《辭海》在泥水里撲騰,眼鏡片上濺滿泥點,卻對著搶救出來的殘卷笑出豁牙。那些泡脹的書頁后來晾在竹篙上,被風(fēng)掀動時,仿佛千百只濕翅膀在撲棱。 臘月里最饞人的是連環(huán)畫柜臺,玻璃板下壓著《雞毛信》的彩色封面,海娃趕著羊群穿過炮火,羊角上拴的紅布條比我棉襖的補(bǔ)丁還鮮艷。我用賣廢鐵的錢換回半本《敵后武工隊》,藏在麥秸垛里讀到月上山梁,羊圈里的老山羊嚼著書角,竟把李向陽的子彈嚼成了草屑。 中考落榜那年夏天,我在麥秸垛后頭翻爛了陳忠實寫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孫少平在礦井下的獨(dú)白,和著谷倉老鼠啃噬稻殼的聲響,竟比語文老師的講解更透徹。月光從瓦縫漏進(jìn)來,照著孫少平給田曉霞寫信的段落,我在裝化肥的麻袋上記下:“痛苦是白石灰,總在生活潑水時發(fā)熱?!睂O少平掏煤的鎬頭聲,和母親在村西自留地刨紅薯的動靜此起彼伏,汗水滴在書頁上,把“命運(yùn)”兩個字洇成了蝴蝶的形狀。黃昏時分的蜻蜓低飛而過,翅膀掠過墻面的瞬間,我忽然看清那些經(jīng)年歲月的煙漬,原來都是漢字被燒焦的筆畫。 后來帶著這句話南下,綠皮車廂搖晃著《人生》的結(jié)局。高加林蹲在縣城橋頭的剪影,疊印在打工妹們捆扎的編織袋上。我在流水線用油墨打批號時,總想起老書店瓦檐垂落的雨線,那些打在書脊上的水痕,原是最早教我斷句的先生,后來聽說老楊頭走了,他兒子在清理閣樓時,發(fā)現(xiàn)我的欠賬本夾在《新華字典》里。那些月牙痕已模糊成褐色的斑點,像遺落在舊時光里的蟬蛻。新開的書店在村東頭,玻璃幕墻亮得能照見云影,可再沒有哪扇木門會吱呀著,吐出一團(tuán)混合著煙草與故紙香氣的黃昏。 去縣城讀高中的前夜,母親用報紙糊墻,泛黃的《人民日報》蓋住了我童年所有的秘密戰(zhàn)場。但媒油燈依舊,當(dāng)我在寒假歸來翻開省吃儉用攢的錢從新華書店買的《百年孤獨(dú)》,布恩迪亞家族的馬孔多小鎮(zhèn)就從墻縫里長出來。母親新添的白發(fā)在光暈中飄動,像奧雷里亞諾上校作坊里融化的金魚。 中元節(jié)去父親墳頭,發(fā)現(xiàn)供盤旁放著一本《徐霞客游記》,書頁間別著一朵油茶花。弟弟說老楊頭臨終前托人捎來的,扉頁有褪色的鉛筆字:“給那個總蹭書看的小子”。山風(fēng)掠過茶樹林,千萬朵白花簌簌地落,恍惚又見那佝僂的身影站在光塵里,竹煙筒輕叩柜臺:“孩子,這本算我借你的?!?/br> 去年清明回鄉(xiāng),老屋已坍塌了半邊,殘存的墻面上,煤油燈熏出的影子依然清晰。我撿起半塊土坯,裂縫里卡著片干枯的南瓜葉,那該是母親當(dāng)年墊在腌菜缸底的。春風(fēng)掠過廢墟時,我聽見三十年前的讀書聲正從墻基深處涌出,混合著母親磨鐮刀的聲響,在暮色中釀成稠密的蜂蜜。 我在書房寫作時,常錯覺有陳年霉味在鼻尖游蕩。小侄女兒說電子書不占地方,她卻不懂有些空間要留著裝時光。窗臺上養(yǎng)著盆瓦松,是老書店殘瓦里長的,月光好的夜晚,肥厚的葉片會泛起類似舊書切口的光澤。這大概就是老楊頭說的“養(yǎng)書的魂”,當(dāng)墨字滲進(jìn)血脈,每個讀書人都會長出年輪般的皺紋。 油茶花又開了,碎白的花瓣落在我給小侄女兒讀的《小王子》上。她指著插圖問我沙漠里的星星會不會冷,我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個蹲在門檻的少年。他衣襟上的鹽漬早化作了月光,而老書店門楣懸掛的風(fēng)鈴,依然在某個時空叮咚作響,那是無數(shù)未讀完的故事,在等著一雙沾滿泥土的手,輕輕掀開扉頁。 如今書房里的落地?zé)裘魅绨讜?,可總不及老屋墻上的光影生動。那些被母親點亮的煤油燈吻過的文字,早化作我掌心的紋路。有時午夜夢回,我恍惚看見林黛玉的竹影在投影儀的白墻上搖曳,而真正的瀟湘館,始終筑在十三歲時老家那面斑駁的土墻上。
?著作權(quán)歸作者所有,轉(zhuǎn)載或內(nèi)容合作請聯(lián)系作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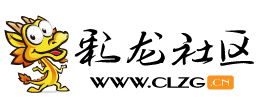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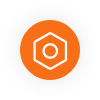
暫無評論,快來評論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