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臺(tái)上的薄荷,今兒個(gè)又悄悄躥高了小半寸,嫩生生的梢頭在風(fēng)里微微打著旋兒,像是在炫耀新得的高度。
記得去年深秋,我從菜市場的垃圾堆旁把它撿回來時(shí),這株小苗可憐巴巴的,葉子蜷曲得像被人揉皺的紙片,黃中帶褐,蔫頭耷腦的,活脫一只淋了冷雨、凍得瑟瑟發(fā)抖的小麻雀,連翅尖都無力地垂著。我尋了個(gè)洗凈的酸奶盒,用鐵釘歪歪扭扭地戳了幾個(gè)透水孔,小心翼翼地把它塞進(jìn)去,又從水龍頭接了半盒清凌凌的自來水,就那么隨手往朝南的窗臺(tái)上一擱,當(dāng)時(shí)真沒指望它能活多久。沒承想,開春回暖,它竟從那枯瘦如柴、泛著淺褐的莖稈里,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憋出了嫩紅的新芽,像極了嬰兒蜷曲的小手指頭,嬌嫩得仿佛一碰就要滴出水來。不多時(shí),葉片便舒展開來,成了翡翠般透亮的小巴掌,邊緣還帶著精致的鋸齒,風(fēng)一吹過,“簌簌簌”地響,那聲音細(xì)碎又輕柔,活像個(gè)受了委屈又重獲溫暖的孩子,在低聲細(xì)語地說著“謝謝呀,謝謝呀”。
這薄荷,真是最不挑揀的性子,卻也最是堅(jiān)韌。陽光慷慨時(shí),它便把每一片葉子都攤開,綠得發(fā)亮,拼了命似的進(jìn)行光合作用,仿佛要把所有的光和熱都儲(chǔ)存在葉脈里;遇上陰雨天,它就知趣地蜷起葉片,像個(gè)乖孩子似的養(yǎng)精蓄銳,一點(diǎn)也不焦躁。水若是澆多了,它默默忍著,哪怕爛了點(diǎn)根也絕不抱怨,只是悄悄調(diào)整;可要是一連旱上三天,它反倒把那些雪白的須根往土里扎得更深更密,仿佛在說:“我才不怕呢!”有一回我出差兩周,心里總惦記著它,回來一瞧,哎喲,可把我心疼壞了——它整個(gè)蔫成了一把曬干的稻草,葉子卷縮發(fā)黃,一碰就簌簌往下掉。我趕緊給它浸了個(gè)透心涼的“澡”,第二天一早再看,嘿!這小東西竟又精神抖擻地支棱起來了,葉片吸飽了水分,綠得能掐出水來,葉尖上還凝著幾顆晶瑩剔透的露珠,顫巍巍的,仿佛昨夜那場瀕死的干渴,不過是場無足輕重的小夢。
前幾日拆快遞,一把沒留神,剪刀尖“噌”地一下蹭到了旁邊伸展的葉片。就在那一瞬間,一股清冽的香氣“噗”地一下在空氣里炸開了!那味道,不像玫瑰那樣甜得發(fā)膩,也不似茉莉那般柔得縹緲,倒像是剛從深山中的冰窖里新汲出來的井水,帶著點(diǎn)沁骨的涼,又混著泥土的清新腥氣和陽光曬過的暖暖味道,一股腦兒地、帶著點(diǎn)霸道地直直鉆進(jìn)鼻腔,瞬間喚醒了昏沉的神思。我當(dāng)時(shí)就愣了愣神,那些被時(shí)光塵封的記憶,竟被這縷香氣輕輕拂開了——小時(shí)候外婆家的院子,墻角也種著好大一片薄荷,綠油油的,挨挨擠擠。每到夏夜乘涼,外婆總愛摘幾片肥厚的葉子,在掌心輕輕一揉,那清涼的香氣便立刻彌漫開來,她再把揉碎的葉片溫柔地抹在我光溜溜的胳膊腿上,一邊抹一邊絮絮叨叨:“抹點(diǎn)這個(gè),蚊子就不咬咱囡囡咯?!蹦菚r(shí)候哪里懂得珍惜,只覺得好玩,常常揪著大把的葉子,在石階上玩“炒菜”的游戲,把好好的葉片揉得稀爛。如今,人在千里之外,反倒被這株從垃圾堆里撿來的薄荷,勾起了心底最柔軟的念想,鼻子竟有些微微發(fā)酸。
薄荷的花,是極小極小的,淡紫色,米粒般大小,星星點(diǎn)點(diǎn)地撒在葉片間,不仔細(xì)瞧,根本發(fā)現(xiàn)不了??删褪沁@毫不起眼的小花,每次我湊近了看,總瞧見幾只黑亮的小螞蟻,排著整整齊齊的隊(duì)伍,在花蕊上忙忙碌碌地搬運(yùn)著什么,不亦樂乎。連平日里圍著旁邊月季打轉(zhuǎn)的小蜜蜂,也會(huì)繞開那嬌艷的花瓣,“嗡嗡”地專程飛到這薄荷叢中,在小小的紫色花粒上落腳,停留許久,仿佛在汲取什么特別的甘飴。原來,這微小的生命,也自有它獨(dú)特的引力場,不必非要爭奇斗艷,也能活得這般熱氣騰騰,有聲有色。
此刻,它又在窗臺(tái)上快活地?fù)u曳著,葉片上細(xì)細(xì)的紋路在陽光下看得清清楚楚,縱橫交錯(cuò),像誰用極細(xì)的綠墨水筆,一筆一畫精心勾勒出的血管,充滿了生命的張力。風(fēng)拂過,那股清清涼涼的香氣便一陣一陣送過來,縈繞在鼻尖。我忽然覺得,這株曾經(jīng)被丟棄、差點(diǎn)枯死的薄荷,或許,根本不是我救了它。
是它,用它那沉默而堅(jiān)韌的方式,在每個(gè)平凡的日子里,悄悄教會(huì)我,怎樣在柴米油鹽的尋常歲月中,把日子過得活色生香,有滋有味。
?著作權(quán)歸作者所有,轉(zhuǎn)載或內(nèi)容合作請聯(lián)系作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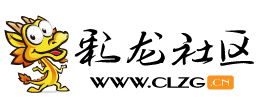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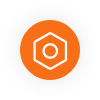
暫無評(píng)論,快來評(píng)論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