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當(dāng)暮色四合,老家淮陽的鄉(xiāng)下便浮起一種聲音,如同晚禱的鐘聲,卻更接地氣,更勾人魂魄:“大椒醬、咸菜絲、八寶菜、西瓜醬豆、五香豆腐鹵、小焦魚、糖蒜、醬瓜、辣疙瘩……”這吆喝聲,早已刻入我的骨血深處,穿透歲月,直抵此刻。這吆喝,是鄉(xiāng)村的鐘點(diǎn),是灶膛引火的信號(hào)。聲音鉆進(jìn)耳朵,像一根無形的線,猛地牽動(dòng)了胃囊深處那點(diǎn)最原始的饞蟲。聽到這聲音,我立刻便丟了手里捏著的土坷垃,粘到母親身邊,拽著她洗得泛白邊緣磨出了毛茬的粗布衣襟,仰著臉,眼巴巴地:“媽,辣椒醬,買辣椒醬!” 母親正彎腰在堂屋門前的咸菜甕旁忙碌。暮光吝嗇地涂抹在她瘦削的脊背上。她直起身,撩起圍裙擦了擦沾著鹽水的手指,那手指常年浸漬,指節(jié)粗大,指甲縫里嵌著洗不凈的褐色。她低頭看我,臉上有疲憊的影子,嘴角卻習(xí)慣性地向上彎起一個(gè)溫軟的弧度,伸手輕輕點(diǎn)了一下我的額角,帶著薄繭的指腹有些糙:“小饞貓,鼻子倒尖。一塊錢,一大碗,省著點(diǎn)吃,莫要偷吃太多,辣心哩?!?/br> 堂屋的門前,那口粗陶的咸菜甕,黑黢黢敦實(shí)實(shí),像個(gè)盤踞了多年的老伙計(jì),沉默地占據(jù)著屬于它的一角土地。甕口蓋著一塊厚實(shí)的木蓋墊。揭開它,一股復(fù)雜而濃烈的氣息便猛地升騰起來——是經(jīng)年累月沉淀下來的老鹽鹵的咸腥,是各種菜蔬在漫長漬泡中發(fā)酵出的微酸,是蒜頭、姜塊、辣椒混合出的霸道辛香。甕肚里,是老鹽水渾濁的天下,沉沉浮浮,腌漬著鄉(xiāng)村日子里的豐饒與匱乏:白胖的蒜頭、碧綠的蒜苔、敦厚的白菜疙瘩、尖利的青紅辣椒、碧玉般的黃瓜段、還有沉在甕底的芫荽疙瘩……凡土地上能生嚼的,皆被母親信手投入這個(gè)甕中,交給鹽鹵和光陰去點(diǎn)化。飯桌上若少了這一口咸菜,那碗里的糊涂或稀飯,便如同失了魂,寡淡得令人心慌意亂,連筷子都提不起勁。 然而,母親每每念叨的“咸菜”,卻獨(dú)指那疙瘩咸菜。這淮陽鄉(xiāng)野土生土長的辣疙瘩,與外面世界稱呼的芥菜疙瘩,分明是兩樣?xùn)|西。外地的疙瘩,圓團(tuán)光滑如小蘿卜,生嚼辣味淡薄,只隱隱一絲芥末油的影子。而老家的辣疙瘩,我們只叫它“辣菜”。切去纓子后,便剩下一個(gè)拳頭大小的圓球,最頂上那一片,密布著深深淺淺的小窩,如同僧人頭頂?shù)慕浒?,透著一股子倔?qiáng)的土氣。生啃一口,那沖鼻的辛辣,直頂腦門,逼得人眼淚都要迸出來。母親從秋末的地里將它們收回,辣菜纓子被仔細(xì)切下,攤在竹席上風(fēng)干,預(yù)備著做小豆腐的引子。那疙瘩頭,才是主角。一個(gè)個(gè)洗凈,攤在檐下陰干表皮的水汽,直到它們顯出泥土賦予的堅(jiān)韌質(zhì)地。母親將它們小心地一層層碼進(jìn)早已洗凈擦干的咸菜甕里,每鋪一層,便均勻地撒上粗糲的大鹽粒子。鹽粒落在疙瘩上,發(fā)出細(xì)微的“沙沙”聲。最后,注入清涼的井水,再舀入幾瓢陳年的老鹽水做引子,直到渾濁的液體完全沒過最上一層疙瘩。她仔細(xì)壓上那塊沉重的老青石——那是多年前父親從河灘特意背回來的腌菜石——然后蓋上木蓋墊,嚴(yán)絲合縫。 母親直起腰,長久地凝視著封好的甕口,仿佛在確認(rèn)一個(gè)重大的契約。夕陽的余暉將她佝僂的身影長長地投在地上。她抬手理了理被風(fēng)吹亂的鬢角,幾根銀絲在暮色里刺眼地一閃,聲音輕得像對甕自語:“好了,該下的都下了,剩下的,交給老天爺,交給日子去養(yǎng)著吧。”甕口閉緊,像一個(gè)緘默的承諾。時(shí)間便如無形的菌絲,悄然鉆入甕中,在那渾濁的鹽水里,在疙瘩坑洼的表皮上,無聲地滋長,醞釀著那獨(dú)一無二的猛烈辛辣。 母親的手藝,遠(yuǎn)不止這一甕疙瘩。腌蔓菁條是周口一帶冬天的恩物。霜降后,蔓菁和青蘿卜被切成粗條,掛在屋檐下,任由北風(fēng)抽干它們的水分,變得綿韌皺縮。煮熟的大豆晾涼,與風(fēng)干的蔓菁蘿卜條混合,撒上足量的鹽、一小撮珍貴的白糖、再淋上白酒和米醋。母親粗糙的雙手在陶盆里用力揉搓攪拌,讓每一根菜條都裹上滋味,最后壓實(shí)裝進(jìn)小口的壇子,用黃泥仔細(xì)封好壇口,擱在陰涼的墻角。個(gè)把月后啟封,那股子混合著豆腥與菜蔬發(fā)酵出的“沖”勁兒,能讓人猝不及防地打個(gè)激靈,鼻腔瞬間通透,額角微微冒汗,渾身的寒氣仿佛都被逼了出來。蘿卜條則另有一番脆爽,鹽糖醋調(diào)和得恰到好處,酸中帶甜,甜里藏咸,嚼在嘴里“咯吱”作響,是喝稀粥時(shí)最熨帖的伴侶。 最顯功夫的是西瓜醬豆。需得窖藏得宜、沙瓤起沙的本地西瓜,配上淮北產(chǎn)的小粒黃豆。黃豆泡漲,入大鐵鍋煮至綿軟而不爛,瀝干水分,趁熱在竹匾里滾上薄薄一層精白面粉,然后攤開在屋角陰涼避風(fēng)處。約摸六七日,黃豆表面便生出一層細(xì)密均勻的灰白色的菌毛。母親每天都要俯身查看,像照看嬌嫩的秧苗。待菌毛長成,再攤在烈日下暴曬幾日,直至豆粒干硬,散發(fā)出一種類似醬曲的醇厚氣息。做醬的日子選在盛夏最毒的日頭下。大瓦罐洗凈暴曬,按母親心中默記多年的比例,曬干的豆粒、大粒粗鹽、挖出的紅沙瓤西瓜肉,一層層鋪入罐中。撒上去的是碾得粗細(xì)均勻的干辣椒末、切得極細(xì)的姜絲,再投入掰碎的八角瓣、一小把香氣霸道的四川花椒。母親用一根長長的磨得光滑的棗木棍,在罐中反復(fù)攪動(dòng),汗水順著她的鬢角、鼻尖滴落,混入那越來越濃稠的醬汁里。罐口用厚實(shí)的棉布蒙好,再用麻繩緊緊扎牢,然后端到院子中央陽光最烈的地方曝曬。每日傍晚,母親必準(zhǔn)時(shí)解開繩索,揭開布,用木棍深深攪動(dòng)一次。醬豆在棍下發(fā)出沉悶的“咕嘟”聲,顏色一日深過一日,醬香一日濃過一日,霸道地彌漫了整個(gè)小院,連墻根下的螞蟻似乎都循著這香氣多爬了幾趟。母親俯身攪拌的身影,在熾烈的陽光下顯得微小卻異常專注,仿佛在進(jìn)行一場虔誠的儀式。日復(fù)一日,直到那醬汁變得深紅油亮,濃稠得能掛住木棍,這一罐飽吸了日光精華的西瓜醬豆才算成了。 臘月初八,日子仿佛自帶一種清冷的儀式感。母親搬出那個(gè)肚大口小的青釉壇子,細(xì)細(xì)洗凈。剝好的蒜瓣,顆顆飽滿如玉,被小心地投入壇中,倒入上好的米醋,要沒過蒜瓣許多。壇口覆上油紙,再用黃泥密封得嚴(yán)嚴(yán)實(shí)實(shí),移到最陰冷的墻角。日子一天天冷下去,壇子里的秘密也在無聲變化。直到年關(guān)將近,打開壇口,一股濃烈酸香撲鼻,壇中的蒜瓣早已褪去雪白,通體化作溫潤通透的碧玉色,瑩瑩可愛,這便是臘八蒜了。母親用小碟子盛出幾顆,酸辣爽脆,是就餃子的絕配。她看著我們吃得咧嘴吸氣,便笑:“臘八蒜,臘八蒜,吃它一冬不怕寒?!?/br> 農(nóng)忙時(shí)節(jié),筋骨像是被地里的活計(jì)拆散又草草拼湊起來。拖著灌了鉛的雙腿邁進(jìn)家門,灶冷鍋涼是常事。直奔堂屋前那口咸菜甕,掀開蓋墊,一股咸酸氣撲面而來,竟比飯菜香更令人心安。伸手在甕中渾濁的鹽水里摸索,撈出一塊沉甸甸的疙瘩咸菜,在水缸邊舀一瓢清水,草草沖去表面的鹽鹵。累得連刀都懶得提,直接上嘴,牙齒狠狠咬下一大塊。咸!辣!沖!那股子猛烈粗糲的滋味瞬間在口腔炸開,混合著汗水的咸澀,一同咽下。就著冰冷的饅頭,大口嚼著。咸菜的咸香、饅頭的麥甜、辣味的刺激,在疲乏到極點(diǎn)的身體里奇異地混合成一種滾燙的飽足感,像一塊燒紅的烙鐵,熨帖著耗盡的力氣和空癟的腸胃。胡亂填飽肚子,往硬板床上一倒,沉重的眼皮立刻合攏。窗外或許還有蟬鳴聒噪,或寒風(fēng)呼嘯,都不管了。一個(gè)短暫渾濁的午覺醒來,揉揉酸澀的眼睛,灌下半瓢涼水,又得一頭扎進(jìn)那似乎永遠(yuǎn)也做不完的農(nóng)活里。 冬日,田野里空曠,時(shí)間仿佛也凍得遲緩。新鮮菜蔬成了稀罕物,辣疙瘩咸菜便從佐餐的配角,一躍成為飯桌上的“硬菜”。母親有了大把的光陰在灶間消磨。她把咸疙瘩切成細(xì)如發(fā)絲的咸菜絲,碼在粗瓷碗里。再切一把冬天窖藏的大蔥,蔥白如玉,蔥葉微黃,也切成細(xì)絲。從另一個(gè)小咸菜壇子里撈出幾顆腌得紅亮亮的咸辣椒,切成小圈。芫荽是奢侈的點(diǎn)綴,只在暖窖里存得少許,洗凈切碎。將這四樣匯聚一盆,澆上深褐色的醬油,淋上幾滴芝麻香油。母親粗糙的手指在盆里翻拌均勻,那混合著咸、辣、鮮、香的復(fù)雜氣味便升騰起來,直往人鼻孔里鉆。拌好的咸菜絲堆在盤子里,色澤誘人,是漫長冬日里最亮眼的下飯恩物。偶爾日子松動(dòng)些,母親會(huì)多滴幾滴香油,那香氣更是勾魂攝魄。一家人圍坐小木桌前,筷子頻頻伸向這盤咸菜,就著滾燙的糊涂或稀粥,唏哩呼嚕,額角冒汗,寒氣便被逼退在門外。母親看著,眼角的皺紋里便溢出滿足,輕聲說:“冬里菜少,咸菜頂餓,也頂好?!彼?xì)細(xì)切咸菜絲時(shí),菜刀在案板上發(fā)出細(xì)密均勻的“嚓嚓”聲,窗外是北風(fēng)卷著枯葉的呼號(hào),那聲音便成了清貧歲月里最踏實(shí)堅(jiān)韌的伴奏。 后來,我像無數(shù)鄉(xiāng)下的少年一樣,被時(shí)代的潮水裹挾著涌進(jìn)了城。城里的超市貨架,如同萬國博覽會(huì),玻璃瓶罐里裝著天南海北的醬菜:琥珀色的榨菜,油亮亮的橄欖菜,甜膩的八寶醬瓜……包裝精美,名目繁多。我也曾買來嘗試,配著精米白飯。那味道,或甜得發(fā)齁,或咸得刻板,或油得膩人。舌頭嘗過,胃里卻始終隔著一層,仿佛少了點(diǎn)什么,怎么也落不到實(shí)處。那感覺,像隔著一層毛玻璃看風(fēng)景,影影綽綽,終究隔膜。一次回鄉(xiāng),剛進(jìn)院門,看見母親正坐在小馬扎上,低著頭,就著午后西斜的陽光,慢悠悠地剝著剛收的毛豆。豆莢裂開的細(xì)微噼啪聲,在安靜的院子里顯得格外清晰。我放下行李,目光掃過堂屋前那口愈發(fā)顯得古舊沉默的咸菜甕,隨口問道:“媽,今年腌咸菜了么?” 母親剝豆的動(dòng)作頓了一下,沒有抬頭,幾根白發(fā)在陽光里格外刺眼。她繼續(xù)著手里的活計(jì),豆粒滾入粗陶碗中,發(fā)出清脆的“嗒嗒”聲。過了一會(huì)兒,她那略帶沙啞的聲音才輕輕地飄過來,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:“甕里還有不少呢,夠吃。今年地里的辣菜長得也蔫,就沒費(fèi)那個(gè)事去腌了。”我一時(shí)怔在原地,喉嚨里像是突然堵了一團(tuán)浸透了鹽水的棉花。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那口甕。蓋墊邊緣的朽爛似乎更大了些,甕身蒙著一層不易察覺的灰,在斜陽里沉默著,像一個(gè)被遺忘的句點(diǎn)。甕口無言,卻仿佛一張深不見底的嘴,封存著那些被鹽鹵浸透的舊日時(shí)光——那些甕中起伏沉浮的菜蔬,曾是她傾盡心力,為全家腌漬下的整段粗糲而溫?zé)岬臍q月。 如今,母親離開這煙火人間,已整整一年半了。 那口老甕依舊守在堂屋前,像一個(gè)被抽走了靈魂的軀殼,愈發(fā)顯得孤寂。木蓋墊邊緣朽爛得厲害,輕輕一碰,便簌簌掉下些碎木屑。我蹲下身,手指有些遲疑地搭在冰冷的甕沿上,用了點(diǎn)力,才將那沉重的蓋墊掀開一條縫。一股微涼撲面而來。甕里空空蕩蕩。渾濁的老鹽水早已干涸,只在甕底殘留著一層薄薄的鹽漬,像一層干涸的淚痕,寂寞地映著頭頂上方那一小片被屋檐切割得方方正正的天空。甕壁內(nèi)側(cè),經(jīng)年累月,被咸菜反復(fù)摩擦擠壓的地方,形成了一圈圈深褐色的印痕,層層疊疊,如同沉入水底的年輪,沉默地記錄著甕中曾有過的豐盈與更替。那些曾在這里沉浮、被鹽鹵點(diǎn)化、最終滋養(yǎng)了我們生命的蒜頭、辣椒、蘿卜、疙瘩……它們早已消融于時(shí)光,無跡可尋。 我伸出手指,沿著甕壁上那圈深褐色的印痕,緩緩地、一寸一寸地摩挲過去。指尖傳來粗糲的沙感,是沉積的鹽粒,是歲月風(fēng)干的漬痕,更是母親那雙粗糙的手,在無數(shù)個(gè)寒來暑往里,無數(shù)次伸入這甕中,撈出生活的滋味,又投入新的辛勞與期盼,經(jīng)年累月摩挲出的印記。這印記,便是母親在這人世間,用最笨拙也最深沉的方式,刻下的無字碑文。 甕底那點(diǎn)鹽漬,在幽暗中泛著微弱的光,像是歲月河床深處凝結(jié)的最后一點(diǎn)咸澀。這口空了的甕,比任何滿溢時(shí)都顯得沉重。它盛放過的,哪里僅僅是鹽水和菜蔬?它盛放過貧瘠土地上的生機(jī),盛放過母親被汗水浸透的歲月,盛放過一個(gè)家賴以存續(xù)的微光,盛放過那些被粗糲生活磨礪出的滋味與暖意。這甕的沉默里,蘊(yùn)藏著一種超越鹽分的咸澀,它無聲地滲入骨髓,提醒著我們,生活最深沉的滋味,往往由最簡樸的容器承載,以最沉默的方式,滲入我們靈魂的最深處。 母親傾盡畢生的鹽粒與光陰,在這甕中反復(fù)腌漬的,何嘗不是她自己?將生命的汁液與滋味,一點(diǎn)點(diǎn)揉搓進(jìn)去,滋養(yǎng)了她的兒女。甕中的鹽鹵雖已枯竭,那混合著泥土與汗水的咸味,早已化作血脈,在我們的生命里奔流不息。它如同母親無聲的叮嚀,在每一個(gè)寡淡的時(shí)刻悄然泛起:人間至味,不過是素手調(diào)羹的煙火;世間至重,唯有那只為兒女傾空自身的舊甕。它空了,卻比滿時(shí)更滿,盛著化不開的咸澀,盛著一個(gè)母親被時(shí)光風(fēng)干的背影。
?著作權(quán)歸作者所有,轉(zhuǎn)載或內(nèi)容合作請聯(lián)系作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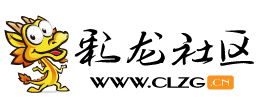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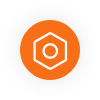
暫無評論,快來評論吧!